求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文《陈毅市长》《威尼斯商人》《变色龙》《我的叔叔于勒》原文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4/28 00: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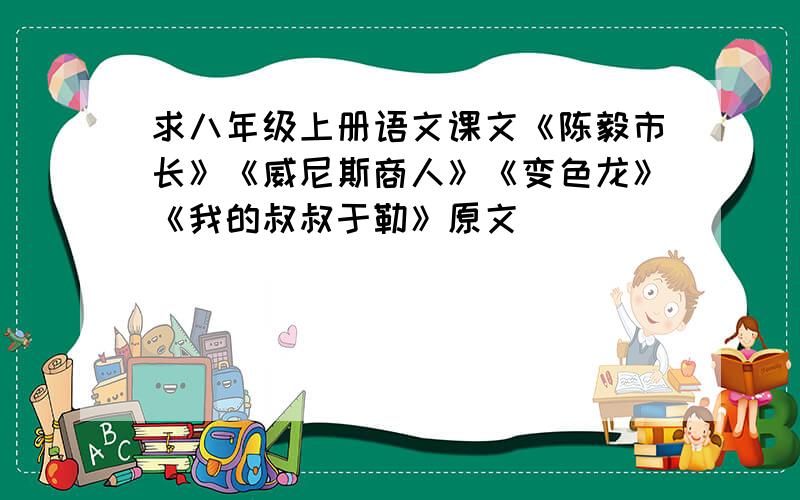
求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文《陈毅市长》《威尼斯商人》《变色龙》《我的叔叔于勒》原文
求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文《陈毅市长》《威尼斯商人》《变色龙》《我的叔叔于勒》原文
求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文《陈毅市长》《威尼斯商人》《变色龙》《我的叔叔于勒》原文
威尼斯商人
公爵、众绅士、安东尼奥、巴萨尼奥、葛莱西安诺、萨拉里诺、萨莱尼奥及余人等同上. 公 爵 安东尼奥有没有来? 安东尼奥 有,殿下. 公 爵 我很为你不快乐;你是来跟一个心如铁石的对手当庭质对,一个不懂得怜悯、没有一丝慈悲心的不近人情的恶汉. 安东尼奥 听说殿下曾经用尽力量劝他不要过为已甚,可是他一味固执,不肯略作让步.既然没有合法的手段可以使我脱离他的怨毒的掌握,我只有用默忍迎受他的愤怒,安心等待着他的残暴的处置. 公 爵 来人,传那犹太人到庭. 萨拉里诺 他在门口等着;他来了,殿下. 夏洛克上. 公 爵 大家让开些,让他站在我的面前.夏洛克,人家都以为——我也是这样想——你不过故意装出这一副凶恶的姿态,到了最后关头,就会显出你的仁慈恻隐(对受苦难的人表示同情.)来,比你现在这种表面上的残酷更加出人意料;现在你虽然坚持着照约处罚,一定要从这个不幸的商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到了那时候,你不但愿意放弃这一种处罚,而且因为受到良心上的感动,说不定还会豁免(免除.)他一部分的欠款,你看他最近接连遭逢的巨大损失,足以使无论怎样富有的商人倾家荡产,即使铁石一样的心肠,从来不知道人类同情的野蛮人,也不能不对他的境遇发生怜悯.犹太人,我们都在等候你一句温和的回答. 夏洛克 我的意思已经向殿下告禀过了;我也已经指着我们的圣安息日起誓,一定要照约执行处罚;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宪章,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要求撤销贵邦的特权,您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接受三千块钱,宁愿拿一块腐烂的臭肉,那我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回答您,我只能说我欢喜这样,这是不是一个回答?要是我的屋子里有了耗子,我高兴出一万块钱叫人把它们赶掉,谁管得了我?我不是回答了您吗?有的人不爱看张开嘴的猪,有的人瞧见一头猫就要发脾气,还有人听见人家吹风笛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小便;因为一个人的感情完全受着喜恶的支配,谁也做不了自己的主.现在我就这样回答您:为什么有人受不住一头张开嘴的猪,有人受不住一头有益无害的猫,还有人受不住咿咿唔唔的风笛的声音,这些都是毫无充分的理由的,只是因为天生的癖性,使他们一受到刺激,就会情不自禁地现出丑相来:所以我不能举什么理由,也不愿举什么理由,除了因为我对于安东尼奥抱着久积的仇恨和深刻的反感,所以才会向他进行这一场对于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诉讼.现在您不是已经得到我的回答了吗? 巴萨尼奥 你这冷酷无情的家伙,这样的回答可不能作为你的残忍的辩解. 夏洛克 我的回答本来不是为了讨你的欢喜. 巴萨尼奥 难道人们对于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都一定要置之死地吗? 夏洛克 哪一个人会恨他所不愿意杀死的东西? 巴萨尼奥 初次的冒犯,不应该就引为仇恨. 夏洛克 什么!你愿意给毒蛇咬两次吗? 安东尼奥 请你想一想,你现在跟这个犹太人讲理,就像站在海滩上,叫那大海的怒涛减低它的奔腾的威力,责问豺狼为什么害得母羊为了失去它的羔羊而哀啼,或是叫那山上的松柏,在受到天风吹拂的时候,不要摇头摆脑,发出簌簌的声音.要是你能够叫这个犹太人的心变软——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硬呢?——那么还有什么难事不可以做到?所以我请你不用再跟他商量什么条件,也不用替我想什么办法,让我爽爽快受到判决,满足这犹太人的心愿吧. 巴萨尼奥 借了你三千块钱,现在拿六千块钱还你好不好? 夏洛克 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做六份,每一份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 公 爵 你这样一点没有慈悲之心,将来怎么能够希望人家对你慈悲呢? 夏洛克 我又不干错事,怕什么刑罚?你们买了许多奴隶,把他们当作驴狗骡马一样看待,叫他们做种种卑贱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出钱买来的.我可不可以对你们说,让他们自由,叫他们跟你们的子女结婚?为什么他们要在重担之下流着血汗?让他们的床铺得跟你们的床同样柔软,让他们的舌头也尝尝你们所吃的东西吧,你们会回答说:“这些奴隶是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也可以回答你们: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你们的法律去见鬼吧!威尼斯城的法令等于一纸空文.我现在等候着判决,请快些回答我,我可不可以拿到这一磅肉? 公 爵 我已经差人去请培拉里奥,一位有学问的博士,来替我们审判这件案子;要是他今天不来,我可以有权宣布延期判决. 萨拉里诺 殿下,外面有一个使者刚从帕度亚来,带着这位博士的书信,等候着殿下的召唤. 公 爵 把信拿来给我;叫那使者进来. 巴萨尼奥 高兴起来吧,安东尼奥!喂,老兄,不要灰心!这犹太人可以把我的肉、我的血、我的骨头、我的一切都拿去,可是我决不让你为了我的缘故流一滴血. 安东尼奥 我是羊群里一头不中用的病羊,死是我的应分;最软弱的果子最先落到地上,让我也就这样结束了我的一生吧.巴萨尼奥,我只要你话下去,将来替我写一篇墓志铭,那你就是做了再好不过的事. 尼莎莉扮律师书记上. 公 爵 你是从帕度亚培拉里奥那里来的吗? 尼莉莎 是,殿下.培拉里奥叫我向殿下致意.(呈上一信.) 巴萨尼奥 你这样使劲儿磨着刀干吗? 夏洛克 从那破产的家伙身上割下那磅肉来. 葛莱西安诺 狠心的犹太人,你不是在鞋口上磨刀,你这把刀是放在你的心口上磨;无论哪种铁器,就连刽子手的钢刀,都赶不上你这刻毒的心肠一半的锋利.难道什么恳求都不能打动你吗? 夏洛克 不能,无论你说得多么婉转动听,都没有用. 葛莱西安诺 万恶不赦的狗,看你死后不下地狱!让你这种东西活在世上,真是公道不生眼睛.你简直使我的信仰发生摇动,相信起毕达哥拉斯所说畜生的灵魂可以转生人体的议论来了;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因为吃了人给人捉住吊死,它那凶恶的灵魂就从绞架上逃了出来,钻进了你那老娘的腌臜的胎里,因为你的性情正像豺狼一样残暴贪婪. 夏洛克 除非你能够把我这一张契约上的印章骂掉,否则像你这样拉开了喉咙直嚷,不过白白伤了你的肺,何苦来呢?好兄弟,我劝你还是让你的脑子休息一下吧,免得它损坏了,将来无法收拾.我在这儿要求法律的裁判. 公 爵 培拉里奥在这封信上介绍一位年轻有学问的博士出席我们的法庭.他在什么地方? 尼莉莎 他就在这儿附近等着您的答复,不知道殿下准不准许他进来? 公 爵 非常欢迎.来,你们去三四个人,恭恭敬敬领他到这儿来.现在让我们把培拉里奥的来信当庭宣读. 书 记 (读)“尊翰(对别人来信的尊称.)到时,鄙人抱疾方剧,适有一青年博士鲍尔萨泽君自罗马来此,致其慰问,因与详讨犹太人与安东尼奥一案,遍稽(查考.)群籍,折衷是非,遂恳其为鄙人庖代(也写作“代庖”,是成语“越俎代庖”(《庄子》)的简单说法.意思是越权办事或者包办代替.这里指代理他人的职务.庖,厨师.),以应殿下之召.凡鄙人对此案所具意见,此君已深悉无遗;其学问才识,虽穷极赞辞,亦不足道其万一,务希勿以其年少而忽之,益如此少年老成之士,实鄙人生平所仅见也.倘蒙延纳,必能不辱使命.敬祈钧裁(恭请做出决定的意思.).” 公 爵 你们已经听到了博学的培拉里奥的来信.这儿来的大概就是那位博士了. 鲍西娅扮律师上. 公 爵 把您的手给我.足下是从培拉里奥老前辈那来的吗? 鲍西娅 正是,殿下. 公 爵 欢迎欢迎;请上坐.您有没有明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审理的这件案子的两方面的争点? 鲍西娅 我对于这件案子的详细情形已经完全知道了.这儿哪一个是那商人,哪一个是犹太人? 公 爵 安东尼奥,夏洛克,你们两人都上来. 鲍西娅 你的名字就叫夏洛克吗? 夏洛克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鲍西娅 你这场官司打得倒也奇怪,可是按照威尼斯的法律,你的控诉是可以成立的.(向安东尼奥)你的生死现在操在他的手里,是不是? 安东尼奥 他是这样说的. 鲍西娅 你承认这借约吗? 安东尼奥 我承认. 鲍西娅 那么犹太人应该慈悲一点. 夏洛克 为什么我应该慈悲一点?把您的理由告诉我. 鲍西娅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我说了这一番话,为的是希望你能够从你的法律的立场上作几分让步;可是如果你坚持着原来的要求,那么威尼斯的法庭是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商人宣判定罪了. 夏洛克 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当!我只要求法律允许我照约执行处罚. 鲍西娅 他是不是无力偿还这笔借款? 巴萨尼奥 不,我愿意替他当庭还清;照原数加倍也可以;要是这样他还不满足,那么我愿意签署契约,还他十倍的数目,拿我的手、我的头、我的心做抵押;要是这样还不能使他满足,那就是存心害人,不顾天理了.请堂上运用权力,把法律稍为变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错误,干一件大大的功德,别让这个残忍的恶魔逞他杀人的兽欲. 鲍西娅 那可不行,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情都可以干了.这是不行的. 夏洛克 一个但尼尔来做法官了!真的是但尼尔再世!聪明的青年法官啊,我真佩服你! 鲍西娅 请你让我瞧一瞧那借约. 夏洛克 在这儿,可尊敬的博士;请看吧. 鲍西娅 夏洛克,他们愿意出三倍的钱还你呢. 夏洛克 不行,不行,我已经对天发过誓啦,难道我可以让我的灵魂背上毁誓的罪名吗?不,把整个儿的威尼斯给我,我都不能答应. 鲍西娅 好,那么就应该照约处罚:根据法律,这犹太人有权要求从这商人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来.还是慈悲一点,把三倍原数的钱拿去,让我撕了这张约吧. 夏洛克 等他按约中所载条款受罚以后,再撕不迟.您瞧上去像是一个很好的法官;您懂得法律,您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不愧是法律界的中流砥柱,所以现在我就用法律的名义,请您立刻进行宣判,凭着我的灵魂起誓,谁也不能用他的口舌改变我的决心.我现在但等着执行原约. 安东尼奥 我也诚心请求堂上从速宣判. 鲍西娅 好,那么就是这样:你必须准备让他的刀子刺进你的胸膛. 夏洛克 啊,尊严的法官!好一位优秀的青年! 鲍西娅 因为这约上所订定的惩罚,对于法律条文的涵义并无抵触. 夏洛克 很对很对!聪明正直的法官!想不到你瞧上去这样年轻,见识却这么老练! 鲍西娅 所以你应该把你的胸膛袒露出来. 夏洛克 对了,“他的胸部”,约上是这么说的;——不是吗,尊严的法官?——“靠近心口的所在”,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鲍西娅 不错,称肉的天平有没有预备好? 夏洛克 我已经带来了. 鲍西娅 夏洛克,去请一位外科医生来替他堵住伤口,费用归你负担,免得他流血而死. 夏洛克 约上有这样的规定吗? 鲍西娅 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可是另又有什么相干呢?肯做一件好事总是好的. 夏洛克 我找不到;约上没有这一条. 鲍西娅 商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安东尼奥 我没有多少话要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把你的手给我,巴萨尼奥,再会吧!不要因为我为了你的缘故遭到这种结局而悲伤,因为命运对我已经特别照顾了:她往往让一个不幸的人在家产荡尽以后继续活下去,用他凹陷的眼睛和满是皱纹的额角去挨受贫困的暮年;这一种拖延时日的刑罚,她已经把我豁免了.替我向尊夫人致意,告诉她安东尼奥的结局;对她说我怎样爱你,又怎样从容就死;等到你把这一段故事讲完以后,再请她判断一句,巴萨尼奥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真心爱他的朋友.不要因为你将要失去一个朋友而懊恨,替你还债的人是死而无怨的;只要那犹太人的刀刺得深一点,我就可以在一刹那的时间把那笔债完全还清. 巴萨尼奥 安东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的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它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出你的生命. 鲍西娅 尊夫人要是就在这儿听见您说这样话,恐怕不见得会感谢您吧. 葛莱西安诺 我有一个妻子,我可以发誓我是爱她的;可是我希望她马上归天,好去求告上帝改变这恶狗一样的犹太人的心. 尼莉莎 幸亏尊驾在她的背后说这样的话,否则府上一定要吵得鸡犬不宁了. 夏洛克 这些便是相信基督教的丈夫!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别再浪费光阴了;请快些儿宣判吧. 鲍西娅 那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是你的;法庭判给你,法律许可你. 夏洛克 公平正直的法官! 鲍西娅 你必须从他的胸前割下这磅肉来;法律许可你;法庭判给你. 夏洛克 博学多才的法官!判得好!来,预备! 鲍西娅 且慢,还有别的话哩.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 葛莱西安诺 啊,公平正直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啊,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洛克 法律上是这样说吗? 鲍西娅 你自己可以去查查明白.既然你要求公道,我就给你公道,而且比你所要求的更地道. 葛莱西安诺 啊,博学多才的法官!听着,犹太人;好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洛克 那么我愿意接受还款;照约上的数目三倍还我,放了那基督徒. 巴萨尼 钱在这儿. 鲍西娅 别忙!这犹太人必须得到绝对的公道.别忙!他除了照约处罚以外,不能接受其他的赔偿. 葛莱西安诺 啊,犹太人!一个公平正直的法官,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官! 鲍西娅 所以你准备着动手割肉吧.不准流一滴血,也不准割得超过或是不足一磅的重量;要是你割下来的肉,比一磅略微轻一点或是重一点,即使相差只有一丝一毫,或者仅仅一根汗毛之微,就要把你抵命,你的财产全部充公. 葛莱西安诺 一个再世的但尼尔,一个但尼尔,犹太人!现在你可掉在我的手里了,你这异教徒! 鲍西娅 那犹太人为什么还不动手? 夏洛克 把我的本钱还我,放我去吧. 巴萨尼奥 钱我已经预备好在这儿,你拿去吧. 鲍西娅 他已经当庭拒绝过了;我们现在只能给他公道,让他履行原约. 葛莱西安诺 好一个但尼尔,一个再世的但尼尔!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说这句话. 夏洛克 难道我单单拿回我的本钱都不成吗? 鲍西娅 犹太人,除了冒着你自己生命的危险割下那一磅肉以外,你不能拿一个钱. 夏洛克 好,那么魔鬼保佑他去享用吧!我不打这场官司了. 鲍西娅 等一等,犹太人,法律上还有一点牵涉你.威尼斯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受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爵处置,他人不得过问.你现在刚巧陷入这个法网,因为根据事实的发展,已经足以证明你确有运用直接间接手段,危害被告生命的企图,所以你已经遭逢着我刚才所说起的那种危险了.快跪下来,请公爵开恩吧. 葛菜西安诺 求公爵开恩,让你自己去寻死吧;可是你的财产现在充了公,一根绳子也买不起啦,所以还是要让公家破费把你吊死. 公 爵 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你的财产一半划归安东尼奥,还有一半没入公库;要是你能够诚心悔过,也许还可以减处你一笔较轻的罚款. 鲍西娅 这是说没入公库的一部分,不是说划归安东尼奥的一部分. 夏洛克 不,把我的生命连着财产一起拿了去吧,我不要你们的宽恕.你们拿掉了支撑房子的柱子,就是拆了我的房子;你们夺去了我的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活要了我的命.
变色龙
警官奥丘梅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粗罗,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象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丘梅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上一群人,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长官!……”警察说.
奥丘梅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象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丘梅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长官,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丘梅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迪林,”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象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迪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说.
“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长官,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长官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象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①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迪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象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丘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奥丘梅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崽子……”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丘梅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继续在市集的广场上巡视.
变色龙
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巡警,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罗筛,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楚蔑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
全部展开
变色龙
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巡警,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罗筛,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楚蔑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楚蔑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上一群人,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长官!……”巡警说。
奥楚蔑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 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 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象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蔑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楚蔑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长官,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 口说。“我正跟密特里•密特里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 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是细致的。这得赔 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长官, 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不错,……”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不错。 ……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 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 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德林,”警官对巡警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 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象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德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 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 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长官,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长官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 胡说,谁象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审判我 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 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巡警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 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呸子。……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 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 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 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叶尔德林,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 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 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是名贵的狗,要是 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 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 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洛诃尔!你过来,亲爱 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 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洛诃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 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来了?”奥楚蔑洛夫问, 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 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崽子……”
普洛诃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继续在市集的广场上巡视。
我的叔叔于勒
我小时候,家在哈佛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15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那时候,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进口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糟蹋钱。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了。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我这位于勒叔叔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10年之久,于勒叔叔没再来信。可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那时候大家简直好象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
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这个小岛是属英国管的。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海,便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个邻国,看看这个国家的民族,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习惯。
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心事,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我们感到快活而骄傲。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
毫无疑义,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个姐姐赞成。母亲于是很不痛快地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又说:"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十分不公道。我一直盯着父亲,看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走去。
我父亲突然好象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母亲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我想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走去。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心里异常紧张。父亲客客气气地和船长搭上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怎样,土地性质怎样等等。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特快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船的船员。"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就冷冷地回答说:"他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据说他在哈佛尔还有亲属,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听说他在那边阔绰过一个时期,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到什么田地!"
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哑着嗓子说:"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您,船长。"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是那么神色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真是他!"然后他就问:"咱们怎么办呢?"母亲马上回答道:"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父亲突然很狼狈,低声嘟哝着:"出大乱子了!"
母亲突然很暴怒起来,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现在把钱交给若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楣的了,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她说完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5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他答道:"2法郎50生丁。"
我把5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找了钱。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等我把2法郎交给父亲,母亲诧异起来,就问:"吃了3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给了他10个铜子的小费。" 我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收起
陈毅市长
沙叶新
(一九四九年冬的一天深夜。化学家齐仰之的家。)
在急促的电话铃声中启幕。
这是一间简陋破旧的卧室兼书房,地板残缺不全,残缺处都从地上冒出一丛一丛青草。屋角结着蜘蛛网。书桌上堆满书籍和化学仪器。一张单人床,卧具凌乱。墙上贴着一些化学图表,还贴着一张醒目的字条:“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本室主人敬白。”室主人显然过的是深居简出的书斋生活,他与外部世...
全部展开
陈毅市长
沙叶新
(一九四九年冬的一天深夜。化学家齐仰之的家。)
在急促的电话铃声中启幕。
这是一间简陋破旧的卧室兼书房,地板残缺不全,残缺处都从地上冒出一丛一丛青草。屋角结着蜘蛛网。书桌上堆满书籍和化学仪器。一张单人床,卧具凌乱。墙上贴着一些化学图表,还贴着一张醒目的字条:“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本室主人敬白。”室主人显然过的是深居简出的书斋生活,他与外部世界保持不多联系的主要手段则是搁在书箱上的那架电话机。
电话铃声继续响着,但齐仰之充耳不闻,一边翻书,一边在做试验。电话铃声停止,齐仰之望着电话得胜似的笑了笑。可是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齐仰之大皱眉头,拿起话筒。)
齐仰之 (极不耐烦地)谁?……你不知道我在工作吗?……知道!知道干吗还来打扰我?朋友?工作的时候只有化合、分解、元素、分子量是我的朋友!……好,你说吧!……不,我早就声明过,政治是与我绝缘的,我也绝不会溶解在政治里。……我是个化学家,我干吗要去参加政府召开的会议?……不去!不去!……什么?陈市长亲自下的请帖?哪个陈市长?……他是何许人?不认识!……对,不认识!……不论谁,就是孙中山的请帖我也不去!……对你算客气的了!要不是老朋友,我早就把电话挂了!……不不不,你别来,你来了也没有用!最近半年我要写书,谁来我也不接待!……好了,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时间到了! (不由分说地将电话挂上,然后又坐下继续工作)(少顷,陈毅上,按门上的电铃。)
齐仰之 (烦躁地)谁?
陈 毅 我!
齐仰之 (走过去开门)你找谁?
陈 毅 请问,这是齐仰之先生的府上吗?
齐仰之 你是谁?
陈 毅 姓陈名毅。
齐仰之 (打量陈毅)陈毅?不认识,恕不接待!(乓的一声将大门关 上,匆匆回到桌边,又开始埋头工作)
陈 毅 (一惊)吃了个闭门羹!(想再敲门,又止住,思索)这可咋个办?真是个怪人!(转身欲走,又停了下来)我就不相信,偌大一个上海我都进得来,这小小一扇门我就进不去。(再次按门上的电铃)(齐仰之只是将头偏了偏。)
(陈毅索性将手指一直按在电铃的揿钮上,铃声持久不息。)
(齐仰之欲发作,气冲冲去开门。)
齐仰之 又是你!
陈 毅 对头!
齐仰之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陈 毅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倒是干大事的。鄙人是上海市的父母官,本市的市长。
齐仰之 (一惊)什么?你就是电话里说的那个陈市长?
陈 毅 正是在下。
齐仰之 那……半夜三更来找我有何贵干?
陈 毅 无事不登三宝殿嘛。
齐仰之 可是我……我在工作。
陈 毅 我专程来拜访齐先生,也是为了工作。
齐仰之 (为难地)好吧。不过,我只有三分钟的空闲。
陈 毅 三分钟?
齐仰之 对。
陈 毅 可以,决不多加打扰。
齐仰之 请。
(齐仰之请陈毅进屋。)
陈 毅 (打量房间)齐先生就住这里?
齐仰之 对,好多年了。
陈 毅 我倒想起了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齐仰之 (高兴地)不不,过奖了,过奖了!
陈 毅 不过刘禹锡的陋室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齐先生的这间陋室嘛,则是“苔痕上墙绿,草色室中青”。
齐仰之 (笑)陈市长真是善于笑谈。
陈 毅 (看到墙上贴的条幅,念)“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
齐仰之 (看表)有何见教,请说吧。
陈 毅 (也看表)真的只许三分钟?
齐仰之 从不例外。
陈 毅 可我做报告,一讲就是几个钟头。
齐仰之 (看表)还有两分半钟了。
(齐仰之请陈毅坐下。)
陈 毅 好好好。这次我趋访贵宅,一是向齐先生问候,二是为了谈谈本市长对齐先生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齐仰之 哦?敬听高论。
陈 毅 我以为,齐先生虽是海内闻名的化学专家,可是对有一门化学齐先生也许一窍不通。
齐仰之 什么?我齐仰之研究化学四十余年,虽然生性驽钝,建树不多,但举凡化学,不才总还略有所知。
陈 毅 不,齐先生对有门化学确实无知。
齐仰之 (不悦)那我倒要请教,敢问是哪门化学?是否无机化学?
陈 毅 不是。
齐仰之 有机化学?
陈 毅 非也。
齐仰之 医药化学?
陈毅亦 不是。
齐仰之 生物化学?
陈 毅 更不是。
齐仰之 这就怪了,那我的无知究竟何在?
陈 毅 齐先生想知道?
齐仰之 极盼赐教!
陈 毅 (看表)哎呀呀,三分钟已到,改日再来奉告。
齐仰之 话没说完,怎好就走?
陈 毅 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嘛。
齐仰之 这……可以延长片刻。
陈 毅 说来话长,片刻之间,难以尽意,还是改日再来,改日再来。
(陈毅站起,假意要走,齐仰之连忙拦住。)
齐仰之 不不不,那就请陈市长尽情尽意言之,不受三分钟之限。
陈 毅 要不得,要不得,齐先生是从不破例的。
齐仰之 今日可以破此一例。
陈 毅 可以破此一例?
齐仰之 学者以无知为最大耻辱,我一定要问个明白。请!
(齐仰之又请陈毅坐下。)
陈 毅 好,我是说齐先生对我们共产党人的化学全然无知。
齐仰之 共产党人的化学?唷,这倒是一门新学问。
陈 毅 不,说新也不新%%%。从《共产党宣言》算起,这门化学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齐仰之 那么请问,所谓共产党人的化学,研究些什么?
陈 毅 社会。
齐仰之 社会?
陈 毅 正是。就以中国而言,这门化学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变化成为新民主主义化社会;就是要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旧中国,变化成为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就是共产党人的化学,社会变化之学。
齐仰之 这种化学,与我何干?不知亦不为耻!
陈 毅 先生之言差矣。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社会若不起革命变化,实验室里也无法进行化学变化。齐先生自己也说嘛,致力于化学四十余年,而建树不多,啥子道理哟?并非齐先生才疏学浅,而是社会未起变化之故。想当初,齐先生从海外学成归国,雄心勃勃,一心想振兴中国的医学工业,可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毫不重视。齐先生奔走呼告,尽遭冷遇,以致心灰意冷,躲进书斋,闭门研究学问以自娱,从此不再过问世事。齐先生之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岂不是当时腐败的社会所造成的吗?
齐仰之 (深有感触)是呀,是呀,归国之后,看到偌大一个中国,举目皆是外商所开设的药厂、药店,所有药品几乎全靠进口:S.T来自美国礼来药厂,叶酸全是日本武田药厂所出,酒精是荷兰的,盘尼西林是英国的。这真叫我痛心疾首。我也曾找宋子文当面谈过兴办中国医药工业之事,可是他竟说外国药用也用不完,再制中国药岂不多此一举?我几乎气昏了……
陈 毅 (激情地)可是如今不一样了。你推开窗子往外看一看嘛,窗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科学也有了光明的前途。如今建国伊始,百废待举,不正是齐先生实现多年梦想,大有作为之时吗?
齐仰之 你们真的要办药厂?
陈 毅 人民非常需要。
齐仰之 希望我也……
陈 毅 否则我怎会深夜来访?
齐仰之 (兴奋得不知如何回答)这……
陈 毅 我知道齐先生是学者,是专家,只可就见,不可屈致,所以我才亲顾茅庐,如一顾不成,我愿三顾。
齐仰之 不不不,陈市长一片赤诚,枉驾来访,如此礼贤下士,已使我深为感动。在此以前我之所以未能从命,一是我对共产党人的革命化学毫无所知,二是……二是我这个知识分子身上还有着不少酸性……
陈 毅 我的身上倒有不少碱性,你我碰在一起,不就中和了?
齐仰之 (大笑)妙,妙!陈市长真不愧是共产党人的化学家,没想到你的光临使我这个多年不问政治、不问世事的老朽也起了化学变化!
陈 毅 我哪里是什么化学家哟!我只是一个剂,是个催化剂。
齐仰之 (笑)但不知陈市长对发展医药工业有什么设想?
陈 毅 我们打算在上海建立全国第一个盘尼西林药厂。
齐